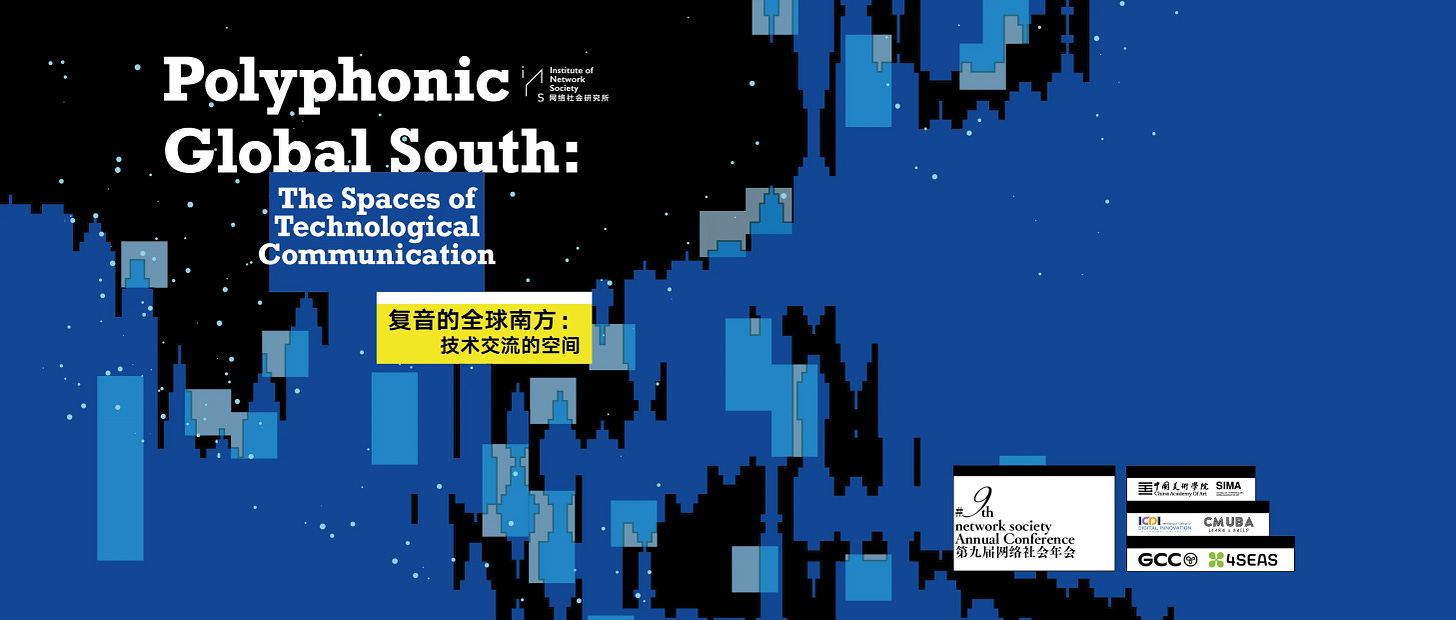第九届网络社会年会|主论坛演讲内容发布
Saskia Witteborn认为全球南方是一种处境。从Web2到Web3,从实体空间向数字领域迁移的过程中,她探讨了菲律宾移民如何通过诸如基于区块链技术和NFT所有权的游戏Axie Infinity边玩边赚(Play-to-Earn),灵活利用系统,融入Web3经济,从而摆脱自身不稳定的生存境况——而不是简单的新技术平台的受害者。(Saskia Witteborn|Web3与区块链游戏:一种南方视角 Web3 and Blockchain Gaming: A Southern Perspective)
同样以菲律宾数字劳工为例,Cheryll Ruth Soriano 超越全球平台的单向权力流动模型,将由社交媒体在线自由职业者发展而成的地方中介组织,引入数字劳动中介基础设施的讨论,填补全球平台和本地劳动力市场之间的研究缝隙。(Cheryll Ruth Soriano|平台、劳动与中介动态)
朱飞达认为Web3不仅仅关乎一种技术,其核心要素是协作智能(Collaborative Intelligence)与代币化经济(Tokenized Economy),即如何把数据所有权及其价值还给人们。而代币(token)本身是“空”的,这意味着它可以捕捉任何东西。(朱飞达|当人工智能遇上Web3:共筑可持续数字经济 When AI Meets Web3: for Sustainable Digital Economy)
回到中国本土,周蓬岸向我们介绍了中国“垃圾佬”即科技拾荒者群体,他们通过回收并再利用废旧电子产品构建可用的计算机及其他设备,形成了从“洋垃圾”到“土垃圾”再到“再制造”的市场和实践。这种草根文化不仅培育了庞大的工程师人才,促进了设备定制和社区创新,更以务实和节省成本的方式应对了市场需求与电子产品浪费问题。(周蓬岸|垃圾佬——以再利用作为平价电子产品的来源 Lā jī lǎo (Tech Scavengers) : Reuse as a source of affordable electronic products)
王洪喆则通过比较中韩早期信息社会,指出中国在1990年代形成了独特的以“发烧友”社群为核心的、自下而上的人文主义数字文化,与韩国自上而下的国家主导型技术发展主义形成对比。然而,这种人文精神已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技术封建主义”,因此主张将数字平台公共化为共享基础设施,并重新审视90年代的价值。(王洪喆|从技术浪漫主义到技术封建主义 From Techno-Romanticism to Techno-Feudalism: A Comparative Historical Study of Early Information Societie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从硬件到社交媒体,Merlyna Lim 提出,数字网络远非平等主义,这意味着少数有影响力的用户控制着大部分数字媒体。她通过草根运动和选举政治案例,分析情感算法是如何超越个人消费,成为塑造我们社会政治格局的重要力量。(Merlyna Lim|情感与算法:解开社交媒体政治的数字核心 Affect and Algorithms: Unpacking the Digital Heart of Social Media Politics)
廖雪婷则通过对互联网上的男性权益运动的分析,揭示了躲在层层技术网络背后基于旧的男性气质形成的有毒的数字男性圈层,正在持续倚仗更高权力如民族主义及反资本主义的庇护。厌女症的平台化不仅是一种表达形式,而且是基于平台的技术驱动治理。而怯弱的、狐假虎威的,必将在缓慢抵抗下被击碎。(廖雪婷|数字行动主义与男性权益运动的民粹主义浪潮 Digital Activism and the Populist Surge of the Men’s Rights Movement)
最后,Payal Arora 认为,一种来自全球北方的悲观主义技术批判,正在阻碍技术基础设施匮乏地区首先能够接入网络、获取技术的使用权。而全球南方地区的技术乐观并非天真无知,而是关于活着,关于经济、人权自由和开放表达的渴望。(Payal Arora|消除数据偏见以建立包容性技术 Debiasing Data to Build Inclusive Technologies)
(*另几位讲者的演讲文稿因涉及未发表期刊内容,将日后更新发布,敬请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