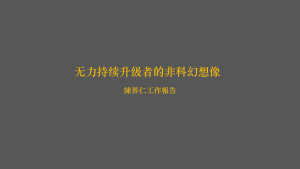第八届网络社会年会|陈界仁:无力持续升级者的非科幻想像
他的生活非常忙碌,疲惫,当然就更不可能对自己的感性提出各种生产的可能
整理/韩佳欣
校对编辑/崔雨 卢睿洋
我的题目叫无力持续升级者的非科幻想像。听完前面两位讲者的精彩演讲,在这边我要讲到的问题是,我们需要先理清楚,传统的无产阶级和有负担的疲惫者的概念,意思是说,传统、古典的无产阶级可能不是有负担,但是今天有很多人是有负担的疲惫者,这个意思是他不是没有收入,而是他的生活非常忙碌,疲惫,当然就更不可能对自己的感性提出各种生产的可能。这些人怎么办?而且这部分人是占绝大多数的。
我先解释一下这个题目的意思。当黄孙权老师邀请我当这个年会的主讲者之一时,我想黄孙权老师是不是“疯了”,他是不是准备在这个非常专业的年会中,安排30分钟的反文化表演,让一个对网络社会几乎无知的外行者与网络的尾端使用者,可以胡言乱语的时刻?虽然我是一个艺术家,但我根本连什么是反文化都不知道,这个表演该怎么进行?我猜想,或许黄老师真的希望在一个专业的年会中,安排一个无力持续升级者,说说他的胡思乱想,这些胡思乱想或许可笑,但也可以作为在当前由公司王国(Corporatocracy)掌控的网络社会下的某种“焦虑症者”的症候案例之一。于是我答应了。
本来我想做一件作品回应这个年会——这件作品是邀请上海所有的外送员,在他们身上装有可侦测其每天行进路线的装置,然后将每个人每天经过的路线,以黑色的线时时呈现在巨大的荧幕上,并且不让这些黑色的路线图从荧幕上被抹去,如此不断的叠加,我想不用几天,全上海的马路都被黑色填满。如果这些黑色的线,是以3D列印的方式,列印在实体的地图上,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黑色的线,像一堵堵不断增高的“黑墙”,无止境的叠高,我猜——不用很久,我们就会发现这些“黑墙”不但把城市变成立体迷宫,更标注出无数外送员的命运,同时也标示出我们的处境——我们都是公司王国实验室的实验鼠。
当然这个计划涉及到的技术与经费太复杂,同时也太大了,我完全做不到。更简单的方式是跟相关公司连线,让我可以时时下载这些外送员的行动数据,但他们应该不会同意吧。
不知道这个计划算不算新媒体艺术?
之所以提出这个想法,意思是说,在我们今天讨论技术问题的时候,不要忘记很多人是不可作为持续的技术上的参与者或者是至少可以升级的人,他们和我一样,我来参加这个讨论会,很怪异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不过是开一个玩笑,可能有点不礼貌。回到这个问题,我的答案是:可能不算。可能因为我看的太少,印象中的新媒体艺术,要不是关于3D或AI制作的太空或虫洞、黑洞影像,要不就是穿越各种时空的超现实景观,还有无数的数字人机合体人,当然大多数画面都有着电脑才有的七彩霓虹般的缤纷色彩,即使是关于歹托邦(Dystopia)的未来世界,“酷”显然是关键词。当然,还有绝对不可少的互动设计。不过我看得实在太少,应该有不少其他形式的新媒体艺术,如同前两位讲者和往届的网络社会年会…。
我还是回到我关心的问题,在不断叠高的“黑墙”下的人,大多时候只能仰望星空或无止境的大楼,当然,我们可以站在“黑墙”下遥控无人机,以无人机之眼帮助我们鸟瞰城市,或是拿着手机看着Google Map以卫星之眼鸟瞰世界(只要Google不要像在这次以巴冲突中,把巴勒斯坦地区的交通流量关闭),只是我们的肉身还是在“黑墙”下。
在回答上述显然太過悲观的看法前,先请在座的诸位,看一段我拍摄于1999-2000年初的短片片段,1999-2000年是股市.com泡沫的高峰期,2001年.com泡沫破灭。影片的片长约5分11秒。
为什么放这个影片?1999-2000是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当时资本与技术结合下形成的席卷全球的科技乐观(投机)主义(至少从一般大众媒体,不是另类群体的观点),但是对此提出警示的平衡观点不够多,或者根本被排除于主流媒体外,而这也是公司王国能持续制造幻觉的核心原因。
此刻随着AI热的兴起,新的科技乐观主义显然已成为讨论人类社会将走向何方的主导叙事,此时,Naomi Klein在 “AI不会‘产生幻觉’,但它们的制造者会。”(AI machines aren‘t ’hallucinating.‘ But their makers are.)一文中,指出科技公司的CEO们至少制造了四种幻觉:一:AI将解决气候危机、二:AI将带来明智的治理。三:可以相信科技巨头不会破坏世界。四:AI将把我们从苦差事中解放出来(这个苦差就比如前面提到的外送员)。
Naomi Klein接着指出这四种幻觉为何不可信,以及这些幻觉是如何遮蔽人类社会解决当前各种危机的关键路徑。关于Naomi Klein的观点,请参阅原文,就不在此赘述。
在讨论相关问题前,我们先简短重提几个众所周知的当前人类社会的危机:
据乐施会(OXFAM)报告,至2023年,掌控公司王国的前81名富豪所占有之财富已超过全球一半人口所拥有的财产总和。
据世卫组织(WHO)报告,仅至2020年,全球患有心理疾病的人数已近 10 亿人,亦即每8人中,就有一人患病。
据世卫组织报告,全球每年约有80万人自杀,平均每40秒就有一人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迁问题小组(IPCC)2023年最新报告,显示地球升温已达摄氏1.1度,若无法在2030年前,将地球温度控制在升温1.5度的临界值内,极端气候将成为常态…。
我的问题是那些科技公司的CEO们所制造那些不难破解的幻觉说词,为何总是一而再的有效?
我想同样放我的一部影片《风摧肉身》(Worn Away)的片段(今年初完成),间接回应那些简单的幻觉为何总是奏效。影片的片段长4分08秒。
谢谢大家耐心看完这部影片。
最后我想说的是——很少有人真的反科技进步,我当然完全不反科技与技术的进步,问题是当前的这些超级技术,已经是由超级跨国公司的极少数股东所共构的“帝国”(empire)所掌控,而且它一点也不虚拟,而是由超级电脑、庞大的伺服器基地与数据中心、卫星链、光纤与无数基地台所构成的超级硬体,而这已不是任何中型国家可以单独完成,更不是传统意义的黑客组织可以颠覆,唯一有可能与“帝国”抗衡的只有中国大陆,但中国大陆在科技与技术的高速发展下,对于什么是合理的人类社会的生活与运作方式,以及人的精神构造问题是否也在同步建构中,也就是黄孙权老师提到的“对齐”问题——我们不要忘了单就中国大陆的官方资料显示中国就有近一亿人患有忧郁症,有至少一亿人的工作状态是被算法严酷控制……。
中国将第一颗量子卫星命名为“墨子号”,我想在座的各位都知道墨家对科学的贡献,更知道墨家的“兼爱非攻”哲学,也都知道墨家学派为何没落,今天不仅是中国,而是整个人类社会除了关注技术问题,不能忘了“兼爱”的意义——亦即,如何将 “人类彼此互爱”的精神,从太空再传回我们居住的行星,这虽不是什么新鲜观点,但却是根本价值,失去根本价值的任何一种技术进步,都只会导致人类社会的危机加速扩大。
我的简短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我的“外行”的表演就到此结束。谢谢。
问答环节
淑丽:我和界仁是很多年的好朋友,也很久没见了,但是由于时间有限我感到很可惜…刚才界仁一直在讲说他是一个非科技的艺术家,他提出一些科技的发展,网络的发展之类的,我觉得对我来讲我发现我们之间的作品是由呼应的,尤其在今天当我讲到《UKI》的cooperation’s control(大公司的控制) 以及他的第二个作品谈到“公司王国”的control。对我感触比较深的是,我自己为什么对科技这么hungry,想用科技来做我的作品,以及界仁比较会退回到他的media(媒体)和approach(办法)的不同,我想这一点和我个人是一个所谓的“少数民族”,不管在国外或是(国内),我的少数民族包装是一个woman(女人),一个Asian(亚洲人),一个酷儿,当然现在又可以增加一个“年纪太大了”,由于这样一个起点,我思考我要怎样去学到科技,用科技去“偷”、“抢”、“借”去“hack”,怎么样用科技来做我的作品的起点,我和界仁关心的题材是有共识的,可是我们的approach(办法)为什么会不同?
陈界仁:我完全不反科技,尤其我最后谈到”墨子号”,我只是要说,我们今天处在各种处境中,我觉得你的方式我完全同意,从最古老的电台到今天讨论的新的科技,我要强调的是网络社会学的重要,因为在部分科技可以颠覆王国公司的掌控的情况下,还有大量的人,像我前面讲到的外送员,还有其他别的人,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办法升级的,所以在我们之间看似有差异的处理办法中,更需要类似网络社会学这样的中介。今天在这两端其实都在反公司王国的掌控,但是我们中间的鸿沟或者落差,需要有不同的方式去把它接起来,这些力量它才会形成更全面性。我最后提到的“墨子”的意思其实是,墨子在那个年代可以被称为“平民共产主义者”,所以淑丽,我,黄孙权我们三者各自做的工作的关系就是要把它串联起来,无力者无法生产出他们自己的感性,我们今天特别需要社会运动,我之所以提到墨子的“兼爱非攻”,如何将 “人类彼此互爱”的精神,从太空再传回我们居住的星球,具体怎么做我不知道,黄孙权提到的“对齐”就是技术要具体地和人类社会对齐,我们要更着眼于技术要做什么,我的想法大概就是这样。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如何把技术下放?让我们可以更简单的使用?应该是六十年代?有一本书叫做《赤脚医生手册》,在中国准备进入全球化,以及整个医疗体系没有办法建立起来之前,这本书非常的棒,针对不同的环境你可以用什么方式去找到相关的草药或者治疗方法…但是我们现在在面对新的时代的时候,好像没有足够的这一类的做事的办法去逾越鸿沟,我其实是这个意思,倒不是批评所有的新媒体艺术,反而那些装饰性的新媒体艺术只是很简单的在现在流行,希望shulea不要误解。
Shu lea:我完全没有觉得你在反科技,所以没有问题的。我只是讲艺术表现的手法,我们必须要把科技人文主义带到这个debate(讨论)来,所以今天早上的讨论就到这,我很期待下午有关AI的辩论,谢谢。
黄孙权:谢谢界仁,谢谢Shulea和Zielinski教授,我做一个短结。我们这个主题为什么叫做”counter-culture”?就是说”counter-culture”并不是”against”(反对),也不是”sub-culture”(次文化),也不是”alternative culture”(另类文化),“counter-culture”其实是一个”site”(基地),在这个基地里面我们要重塑各种技术传播应用的可能性,重要的是怎么把这个基地建立起来,这个基地有时候在艺术作品里面看得很清楚,在好的研究里面看得很清楚,有时候可以从某一些理论上得到很多东西,但如果你不经过实验,不经过尝试,“counter-culture”最后只是变成一个”fashionable culture”(流行文化)而已,这样我们才会觉得“counter-culture”有不同层次的意义。谢谢各位的参与。
讲者简介
陈界仁
1960年生于台湾桃园,目前生活和工作于台湾台北。陈界仁长期和失业劳工、临时工、移工、外籍配偶、无业青年、社会运动者等进行合作,并通过占据资方厂房、潜入法律禁区、运用废弃物搭建虚构场景等行动,对已被新自由主义层层遮蔽的“人民”历史与当代现实,提出另一种“再-想像”、“再-叙事”、“再-书写”与“再-连结”的拍摄计划,他将相关拍摄计划,称为“创噪”与“生产第二层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