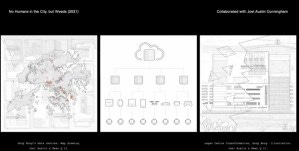第七届网络社会年会|城市论坛 香港场 “徐徐入底流:围绕P2P的微型自治艺术实践与询问” 全程回顾(下)
(2022年11月28日)
第七届网络社会年会城市论坛香港场
“徐徐入底流:围绕P2P的微型自治艺术实践与询问”
论坛嘉宾:黎肖娴,孙咏怡,展销场,杨静,Kwan Q Li
论坛召集 & 论坛主持:张子木
论坛助理:刘磊
编辑整理:马雅,王思云,张钰彬,翠玉
边缘叙
演讲人:Kwan Q Li
Kwan Q Li 的创作涉猎录像、摄影、装置、表演和写作,在跨学科背景下探索建制、科技政治和文化势力的矛昏。毕业于牛津大学纯艺术学士和麻省理工学院艺术、文化和科技硕士。获得奖项包括牛津Stuart Morgan 艺术史论文奖、麻省理工学院Enterprise Poets写作奖及Harold and Arlene Schnitzer Prize。
感谢子木的介绍,也特别感谢 Linda 邀请我加入这个小组。我很喜欢其他演讲者的分享,非常有启发性。由于我是最后一个发言,让我较为散漫(discursive)和遥距地回应这个话题。
今天我将围绕子木在论坛引言中所说的“激发”(Provocation),利用交叉性 (intersectionality)和跨物种(interspecies)方法来扩展 peer(伙伴)的概念;从女权主义解构欧洲中心主义的人类”man”模式,反对人类中心主义,因此我亦较倾向将peer这一概念扩阔至人类和人类以外(more than humans)。如果 P2P 在众多定义中皆被视为由草根大众(grassroot)出发的模型,那么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沿此推进,真正回到草(grass)和根(root)本身。
正如论坛的标题所示,Web3 的开发本质上是 P2P 实践的一种,今天很多嘉宾亦已谈到了诸如共享、开源、民主参与、社会参与实践等观念。在扩展的 P2P 概念中,一个充满更多可能性的社群中不仅包括人类,而且也超越了人类。这样就将生态关切带入了 Web3 的潮流,这也是我稍后会详细谈论的,有关新型网络兴起对环境的影响。今天我将介绍3 个项目,分享我个人对于网络技术的好奇与探索是如何被有关生态的热情塑造的。
多年以来,我一直被城市中的杂草吸引——或许是由于它们一种不被渴望,不被权力重视,处于边缘的状态。
图中所示的是2017年的西九文化区。这区过去十年一直是在工程中,直至今天仍是。杂草是一个人为的分类,用来区分不符合人类期望的植物,杂草是特定语境中不受欢迎的标志。当杂草(weed)由名词变为动词(weeding),表示的是它自身的消除。对我来说,这就是暴力的一种表现——我们的语言在重新命名这些野生植物后对它们造成伤害。但我选择从杂草中看到生命力和表现力。
杂草不经过任何中心编排,亦没有指定的植物类;它只是一个概称,突出了一种匿名性。但也许正是它们的微不足道才是存活下来的原因。不知何故,我们总是把它们视为理所当然,把它们当作背景。杂草这种自我去中心化和自我隐藏的特点,令人重新思考主体性。
在过去的 5、6 年里,我总是在出走和留学。所以我的城市杂草观察也有一些游牧的性质。当我们超越地理空间的限制,是否会对杂草的体验有所不同?杂草是一种生态的多重展现,还是由不同地缘政治起源所区分的许多现象?
我经常将杂草的民族志研究视为了解陌生城市景观的一种方法。我越来越发现,这种显微的观察可以反映出宏观的局势。例如,上面这张照片拍摄于 2017 年的雅典,当时雅典正经历经济衰退,我们可以轻易看到杂草布满了废弃的建筑工地。
又例如是杂草都被灰尘染上了色,在受污染的地区挣扎着生存。
又例如是横跨反映时代物体的杂草,如图中所见的MoBike。
或为监控掩饰的杂草;
又或是见证了历史浮沉的杂草⋯⋯这种关于杂草与城市类型之间关系的显微观察让我想起了菲利克斯·瓜塔里(Pierre-Félix Guattari)的《三种生态学》。他指出生物、社会关系和环境并非三套独立的问题集;它们之间总有一种持续的相互作用,反映了一种更总体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以抗衡现今时代,尤其是技术官僚(technocratic )带来的失衡。这些充满活力,无穷无尽的城市杂草,呈现一种生态的实践,其解域(deterrorising)的力量是对于新配置的发现和重新发现。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冲突与互动,展现在杂草束缚、遮蔽、伪装并装饰着城市基础设施的种重磨擦(rupture)中。
另一方面,我和杂草的相遇只是一种偶然,并无制于科学性的图学关联。很多人问我是否以任何系统化的方式存档杂草的照片,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意图避免任何可能的学术分类形式,或者说就是经典的植物学等级制度。
问题在于,Web3 的大规模发展已经表明它本身即是一种传统资本价值的复制品。Winnie在介绍 NFT 时已经稍微提及。但从我个人的观察和与同伴的交流来看,总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即目前虽然已有大量资金投入科技艺术的发展和 NFT 投机,但在这种科技艺术的浪潮中,是否有足够的关注放在内容本身或其在文化上的角色呢?我认为 P2P 的宝贵之处就在于它能够提出一些另类的价值观,有别于效率、成果、精确性等重复性的模式。创建 P2P 并不是为了证明我们可以做得比其他的网络更好。我们应该问的问题是,什么是更“好”?我认为Elaine的“后勤慢递”对此做出了非常好的回应,这个低技术的想法打开了许多新故事的可能性,如果我们只依赖于主流的叙事结构,那么这些故事将不会被看到。所以 P2P 的意义就在于创造一种另类方法论的原型。
在这个关于杂草的项目中,我从詹姆斯·艾吉(James Agee)的《现在,让我们赞美伟大的人》(Let Us Now Praise Famous Men)中获得灵感,这是一本记录美国大萧条时期农民的摄影-文集,艾吉写道:“在直观的世界中,对于能够辨识它的人来说,一切都是可辨识的,既不需要解剖成科学,也不需要消化成艺术,而是用整个意识去感知它,看到它本来的样子。” 我从杂草中观察到一种由下至上、散漫性、不期而会的力量,绕过划定的界限,进入城市结构的边缘。杂草具有在主动和被动之间漂移的活力,难以被分类和界定,变化不定就是杂草的魅力。
这种对杂草特质的思考一直伴随着我,并显现在其他作品中。在 2019 年至 2021 年期间,我与建筑师和研究员Joel Austin Cunningham开展了一个合作项目“不再荒烟,只余蔓草”(No Humans in the City, but Weeds)。
我们探讨了在香港密集的城市结构中数据中心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现象。也许很多人都不知道,在香港这个土地资源如此紧缺的地方竟然拥有 50 多个数据中心。换句话说,我们关注的是看似虚拟和无形的互联网如何在密集的城市中实现数据的实体化。与西方国家那种典型的大规模结构不同,香港的数据中心大多位于废弃的工业建筑,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经济结构的转型。
正如项目名称所示,我们可以将杂草视作居住在缝隙和裂缝中的城市边缘游牧民。未来我们的生活方式很有可能会持续向线上领域迁移,我们的实体景观会更多地迎合这些网络基础设施或建筑以支持我们的线上活动,而我们则可能成为城市景观中的杂草。比如说,在新冠疫情居家封锁期间,我们基本都是远程办公,没有面对面的社交活动,这将导致对于物理空间的需求发生根本性的转变。
另一方面,我们也意识到这些耗电量巨大的数据中心对于环境的巨大影响,当下的城市持续受到挑战,需不断调整以适应这些 24 小时不间断运行的高温机器。视频中所有的场景都是在香港,有建在填海地上的数据中心村庄,也有正在被改造为数据中心的工业建筑。我希望这个项目可以关注到网络世界对于生态环境的影响,同时考虑在这种巨大的拓扑变化面前,我们如何挽回我们自身的存在。或许我们可以从杂草的灵活性和敏捷性中得到一些启发,以在未来建立新的网络和共同体。
我们为项目创造了一个网上档案库(参见https://nohumans.city),承载着文章、相片、影片、平面图等、供大众参阅。
我今天要分享的最后一个项目同样受到生态形式的启发,对于这个项目来说,是根茎和混合体(hybrid)的概念。这个项目叫Chimera(参见 https://chimera.place),是一个实验性的读书会,尝试将一些理念付诸实践,比如我之前提到的杂草的匿名性,并探索可以替代纸上交流的形式,比如颜色、形式、手绘草图、笔记等等。
该项目始于 2021 年夏天,由 MIT 的Transmedia Storytelling Initiative资助。我和计算机科学家和建筑师 Kii Kang(见:https://k–kang.com/ )合作打造一个线上平台,持续开展读书会活动。目前我们已经进行了 3 轮,每轮持续 2 个月,共计约有 20 名参与者。我们这一群书呆子们希望尝试一种新的阅读形式,或许也与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的实践(L‘invention du quotidien)》相呼应,重新思考我们如何能转化日常事务和行动以作积极的探索——这也是今天很多演讲者都有提到的。
那么这个项目具体是怎么运行的呢?每轮读书会有 6 至 8 名参与者,每个参与者自行选择一份阅读材料,我们刻意没有设置阅读主题,任由主题在讨论中自由发展。当我们集齐所有参与者的阅读材料之后,会在成员之间互相传阅。每个参与者都会在一两周内匿名阅读并评注阅读材料,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人在评注时用了假名。随着时间的推進,阅读材料会收集到越来越多来自不同读者的想法和痕迹。这种强调匿名性的方式鼓励了在没有任何背景或地域包袱和形成共鸣的压力的情况下自由交流思想的氛围。
我们组织这个读书会是想证明阅读并不一定是一种孤独的行为,它也可以成为一个社交的场所,这个想法有点和Winnie介绍的关于开源书籍和合作翻译的工作坊相呼应,而且我还从Elaine的幻灯片中看到一句非常触动我的引言“阅读作为多元的聚集”(reading as a gathering of multitudes)。在传统的读书会中,每个人都会阅读相同的内容然后一起讨论,但我们的另类读书会试图创造一个轻松的环境,让大家在不断地阅读和交谈中进行思想交流。
2021 年夏天我们进行了一次试点读书会,我们与参与者之间只通过电子邮件联系,所以收集阅读材料和回收阅读评注是一个非常耗时的过程。在 2022 年初,我很高兴 Kii 以及 Charles Wu 以及其他我在 MIT 认识的电脑工程师加入了团队,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多用户在线平台 chimera.place,可以更为方便地进行交流。这个网站也是开源的。当参与者登录网站后,ta们会看到时间线页面,阅读内容会逐周出现,ta们可以随时登录并在一周内下载最新的阅读内容,然后通过网站上传ta们的评注。这种流通方式也强调了集体责任感(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因为我们需要收集所有循环中的阅读材料再重新分配,如果有人没有及时上传材料,整个过程将无法继续。
纵然项目讲求匿名性,我们每周亦设有不同的社群题目(social prompt),让参与者每周上传评注和社群回应,例如投影片中所示,我们请求参与者分享他们读书环境的图片,这是为了在不暴露彼此身份的情况下建立一种社群感。有时我们会请参与者分享书中喜欢的句段或觉得最有趣的评注,甚至让ta们录制自己的阅读环境并上传声音文件。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进一步尝试不同的感官体验并保持阅读小组的互动性。
读书会结束后,参与者们将基于所有流通过的阅读材料共同构建一个参考书单(bibliography),其中也包含与主题相关的其他书籍,这像是整个读书会的一个纪念。目前我们准备把这些资料发布在我们的平台上,形成一个由参与者生成的开放资源知识库。
虽然读书会的全过程是匿名的,但活动结束以后我们会在线下相见,进行简单的自我介绍并交流参加活动的感受,并对下一轮活动提出建议或想法。之前的 3 轮都是在波士顿组织的,目前我们正在考虑组织不同语言的读书会,有中文或者韩文的。我们还想组织更多本地化的团队,也希望有机会可以在香港组织,把阅读视作社交活动和生成性网络的理念传递下去。
张子木:谢谢 Queenie(Kwan Q Li)的分享,我觉得你似乎串联起了前几位嘉宾分享的内容,尤其是城市计算基础设施在如今这个城市资源有限的情形下落地的状况。我想问一个问题:同样作为组织者,我非常好奇:
Chimera 读书会中的参与者是如何被选中的呢?感觉就像一個半黑盒,有躲藏成份亦有展示成份。阅读内容是如何选择的?作为组织者是否会对阅读主题进行干预和筛选呢?
Kwan Q Li :我们对阅读的类型没有任何偏好,从大众文化到学科专著都有。从目前为止的参与者的分享来看,这也是一种乐趣,因为ta们真的不知道下一个读物会是什么,这迫使 ta 们走出自己的舒适区,去读 ta 们从未想过会去主动阅读的书。我们也在考虑是否应该設計一些主題,或提供一些引导,之后会继续探索的。关于参与者我们也没有选择过程,因为这个项目刚刚开始,主要依靠朋友之间的口口相传和群发电子邮件。如果有很多人回应,我们就会分成好多组。因为通常一个阅读材料会持续一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如果有六個参加者本会有六份读本,亦即是会持续 6-12 周,所以小组的规模不能太大。目前这个项目仍在测试阶段,欢迎在下一期加入我们,一起探索新的可能。
张子木:好的,接下来我会来念一些来自 Slido 的问题。
Slido 提问:感觉您刚才展示的视频剪辑中,有一种强烈的审美选择感,非常强调形式,但形式和信息之间的联系是什么?这个半成品有点隐蔽,非常沉溺于一种蓝色的城市景观的怀旧感,这与真正的行动有什么连接呢?
Kwan Q Li :我想我不能避免带入我自己的主观意识。我对香港那些数据中心实际上有很强烈的个人感受,它们位于曾经有人类居住过的建筑中。我们对于自己所路过的建筑或景观都是很陌生的,要不是注意到那里不间断发出的轰鸣声,你永远不知道这些看似普通的工业建筑中实际上是布满了服务器的非人空间(non-human space)。这种强烈的异化感和 Allison(杨静) 所说的“绝望”有一点相似。我在作品中尝试带入更多的感觉而非解释性的东西,观察现象,做研究,用图表将其可视化,用镜头来捕捉我在这座城市中看到的外于此种现象的情感,也许这就是美学或形式发挥作用的地方。但我想说的是,我的这个项目实际上与我们会议的主题(去中心化平台及 P2P)有一定的距离,我的作品并不类似于开源或代码生成的作品形式。我也很好奇 Linda(黎肖娴)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因为刚刚我对在她面前展示这些视频感到有些紧张。
黎肖娴:我没有特别多要说的。我想我不会把你的视频作为一种东西,那会取代你的论述,视频就是视频。当你刚才描述视频的时候,我感觉到视频给了一种我可能不会有的非常独特的空间感,这也是为什么你的特定类型的艺术形式需要在空间发生,这是其他艺术形式做不到的,所以这不能作为你谈话的说明或取代你关心的东西。我很高兴从今天所有这些讨论中听到和看到一些非常具体和可行的东西。我确实感到有一种距离,因为我这一代人,或者也许因为我的年龄,也许因为我的关注和我的研究工作,我想听到的更多的东西没有得到广泛的讨论,这不是指责,这只是为了使我观察。这里的四个发言人专注于通过做事情使生活变得更好。我觉得我的坚持似乎是非常遥远的,我觉得我有一种紧迫感,如果我现在不做点什么,那就太晚了。我不能诉说我所做的工作和项目的细节,但我感到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如何在远离中心的地方生活。在一种网络环境中,当我展示那两张关于服务器的照片时,似乎每个人都必须通过它来获得回应或传播知识,我正在做的项目非常迫切需要庇护,躲避、逃避大众。这些思考的部分原因可能是我作为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事情需要被保存,但这有助于我在再次提出这些大问题之前,制定一些更直接的行动。
或许Winnie(孙咏怡)也能分享一些她的观点。
孙咏怡:我好像没有特别具体的观点可以分享,但我觉得或许也有其他的项目,即便它们的语境……我觉得我很喜欢做选择,你得在项目中做些选择,对吧?例如选择出你在某一特定语境下要依靠这一个项目讨论的事情。或许在别处也有很多其他的项目,像是烹饪项目,又或者是更政治的项目,也是非常具有紧迫性的,但它们的语境可能是不同的。
黎肖娴:噢,我真的在做一个档案馆项目,这个项目主要是保存香港在过去四十年内被制作的一些视频。这是一个具有紧迫性的项目,它的紧迫性也在于如何在不被干预的状况下被自由地访问,关于这点我不能说太多,但总而言之它对我而言是具有紧迫性的。
与此同时,我也做了很多工作,致力于让人们不是出于美学的满足制作视频,虽然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它的一部分,但它更关乎向非艺术家开放意识形态的使用。之所以要这么做,是因为我们需要开辟尽可能多的发言场所,说出我们的想法,表达我们的感受。对我来说,这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语境下,只是去站在我的立场上分享我所感知到的紧迫性。
问答环节
张子木:现在聊天框里出现了一个与之非常相关的问题,我想请在座的各位都聊一聊自己的看法:
“感谢诸位令人振奋的演讲,请问各位是不是愿意谈谈各自项目中女性主义或酷儿议题的面向呢?在今天的“ P2P ”主题下欣赏各位的作品时,女权主义会不会是一个突出的标签?感谢。”
这个问题我想先请 Allison(杨静)来回应。
杨静:我工作的视频游戏领域是一个非常男性主导的领域,无论是在内容方面还是在从业人员方面。这也许有一些积极的工作。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总是可以批评视频游戏和视频游戏文化中的有毒文化,但作为一个活动或社区组织者,现在资源有限,有一些小的变化,例如如果有一个女性设计师,可以首先邀请她,虽然女性设计师没有很多,但她们都非常优秀。她们不仅想分享技术或创意知识,还想分享个人的困境,比如如何在这个领域生存,并鼓励女性参与者。确实有很多女孩会以 “我真的很笨”、”我不善于玩视频游戏 “来开始她们的谈话,但加入进来以后,她们就会纠正这种想法。对我个人来说,因为人们现在知道我的这些项目,ta们会找到我以获得一些代码,这是一个类似于新闻界的事情,比如你需要守门人然后把期刊介绍给其他人,这真的很重要。我也做过关于女性的游戏,今年年初,我写了一篇文章被骂得很惨,有太多的贬低来填充真正的观点,这是粗暴的转换。这篇文章激怒了很多男性玩家,他们都是我的读者。但写完之后,我发现开始有一些女孩和我交流,她们说写文章是一种方式,做一些另类的内容是另一种方式,如果ta们不做,我们必须自己做。现在我们有一个社区,不是一个性别墙社区。应该有更多的女性,比如说女性现实的内容,可以诉说男性或女性,可以一起做。这就是我的回应,谢谢。
张子木:其他讲者,也欢迎你们随时加入这个问题的讨论。
黎肖娴:其实我早就料到这个问题会被提出来。每次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时候,我都想问问提问者,你说的女权主义是什么意思?在我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说我们是或不是女权主义者之前,对我来说,这将女权主义的悠久历史缩减成了一句话。我认为在这一点上非常重要的是反本质主义,反二元论,尊重差异,或者是 Queenie(Kwan Q Li)之前说的反混合,我们在谈论很多反等级结构。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能把自己限制为艺术家、技术专家,要么是人文科学的人,要么是对科学感兴趣的人,要么是玩耍的人或阅读的人等等。真的是因为我开始走出这些等级制度和这些二元对立的对立面,我才体验到了能够更自由的畅游。可以说,这并不总是容易的,几乎不可能说我的哪项工作或哪部分工作有女权主义或酷儿主义的一面。
孙咏怡:我还挺同意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说,酷儿视角不仅在于性/别(gender)和性取向。Linda 刚刚提到的“流动性(fluidity)”以及她刚刚举的例子…
黎肖娴:还有“混合性(hybridity)”。
孙咏怡:对,“混合性”和“流动性”也通过我们所选择的方式引导着艺术和科学的空间。但同时,我也天然地觉得酷儿是政治的,它关于挑战既有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还关于了解权力不对称的动态性和不平等性。而我从今天几位讲者分享中,也发现这些听起来相同的大术语的不同部分正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发生在几位讲者各自的工作中。换个方式想想,这就像是询问我们的文化正如何被常态化。对我来说,酷儿概念在于去疏通这种常态化。在于以政治的视角去看,去问,这一切被正常化的东西是何以被常态化的?它们背后的假设是什么?通过它们看到我们社会权力的不对等。我想这就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应。
张子木:展销场,Queenie(Kwan Q Li ),你们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展销场:就像我们的项目对流通的关心那样。如果讨论起书来,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展开非常丰富的关于书本内容的讨论。但我的演讲根本没有提到任何一本我们所销售的书的内容,对不对?因为它不是最重要的。或许是因为我的出生世代和工作的方式缘故,我认为女性主义标签并不是我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而这是我在工作中处理整个系统的方式。讨论或描述酷儿实践似乎在于如何行动和思考以松动某些具体的霸权,但这不一定总是需要被主动和直接地强调出来。如果你观察我们工作的方式,或许会认为我们确实是女性主义的,但反过来想,如果我们今天的论坛阵容是全男性,你会因此向他们提问他们作品中的父权面向的问题吗?
Kwan Q Li :说实话,有部分男性朋友会跟我说他们感到”没资格”参与女性主义相关的讨论,这对我来说感觉太糟糕了。我想制造空间是十分重要的。这个话题在于我们都能意识到自己是系统里的一部分,去思考如何打破边界和僵硬的分类。我觉得所有人都可以对此有一些思考,并进行一些女权和酷儿主义的实践。
张子木:我很开心今天能组织这样一场论坛,在不必过多解释的情形下邀请我心中的女性主义者们与会,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令人开心的事。我们很常见到一些非常清晰地,甚至带着挑衅来讨论性别议题的情形。有时是去强调权力之动态性,或是揭露权力体系背后各异的社会性,试图去超越一种二元对立的思考方式。所以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确实应该预先表明我们的女性主义立场;但我也同时认为,在今天与会的每位嘉宾的实践中,我们都能看见女性主义的议题是如何自然地被囊括进去——并不是以一种“口号”的形式,而是作为一种我们言说、沟通、交友和建立友爱(kinship)的方式。
我们还在 Slido 上收集到了一些问题。麻烦 April 将问题发到聊天框中。各位可以随意选择 1-2 则问题来回应。第一个问题很有意思,我想我现在知道是谁在提问了。这个提问者是一个来自杭州的年轻学者,在这次年会的青年学者论坛也发表了一篇关于情书写作的论文。他说:
Slido 提问:Linda 博士,作为一个直人(straight people),我对爱的交流和表达会是完全失败的吗?您的电子文学实践中情感的面向是如何的呢?1952年克里斯托弗·斯特雷奇(Christopher Strachey)的“情书算法”在我看来是一种对异性恋爱情话语的忧郁的“queer critique”——克里斯托弗和他的合作者阿兰.图灵(Alan Turing)都不是直人——所以我很好奇您写作机器中类似的情感关切。感谢。
黎肖娴:异性恋者谈论爱情有什么不对的吗?首先,我想我需要回应一下,当然,就像我们谈论父权制与女权主义或资本主义与其他类型的替代经济一样,那里已经有一个权力结构,但我认为,我一直在谈论的工作不是要区分一个人的性别取向才允许 ta 发言。但因为工作本身主要是变成一种开放的工作,而开放的工作有很多标准,其中一些是关于不要把自己从突然的更有权威的当局变异的创作模式中去除,比如说在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强大的概念之前,要有一个强大的执行。对我来说,这称为一种工业化的创作模式。我可以在这里谈论更多的东西,这也是我为什么要从自动主义开始的原因——开放的工作和生成艺术的美,因为它有内在的开放性,所以无论谁发言都是代表这个人自己的主体地位。我不确定我是否回答了你的问题,因为我发现这个问题强调了一些我不太理解或同意的假设,我在这里看到的是为什么这是一个问题。我不关心其他哪个机器诗人做了什么,因为它们已经做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喜欢它。但我认为这是关于我为什么追求数字诗歌一个非常明确的原因,我实际上也在写诗,发表了充满情感的诗歌。我对自动主义的方法非常感兴趣,自动主义的方法,就是它允许我们将自己隐藏的主观性找到渠,甚至达到震惊自己的效果——这是我的声音,这是我写的东西。我想这基本上是我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的,我很高兴在这之后可以继续这个谈话,它引发了很多很好的问题。
张子木:或许我们可以在私下谈论更多关于情书写作的问题。除了以上问题外,我们还收到几则提问,我想或许各位可以将对这些提问的回应融合一下。第一个问题是:
“去中心化的合作过程中出现冲突,如何解决,如何协商?”
第二个问题来自周蓬岸,他也是研究网络社会领域的一名学者。他的问题是:
“我刚刚买了一个 Forkonomy NFT,它很便宜。但我的 tezos 却是币安上买的,这非常的不去中心。我看到 Forkonomy NFT 购买教学中建议从 Moonpay 购买,但是其最小购买额度是 280 港币,这个最低消费是个相当高的门槛,同样也是中心化的入口。如何看待区块链使用上难以避免的中心化入口的问题?”
第三则问题是和实践相关的:
“台湾的社群会不会拿到钱?或者得到其他的价值回馈?”
孙咏怡:“Forkonomy”项目不仅仅是把水变成 NFT,而是真的将它装瓶,它是有实体的,可以被用作实际交换。“购买教学” 是由一个台湾 NFT 买家提出的,它就像一个用户指南,因为我们其实是通过人们的贡献构建起一个社群。如果你觉得,有其他类型的钱包是更好的,那么我就觉得你就应该去更新它,这也是一种不断改变访问和评估 NFT 或钱包之类物什的方式。
另一个问题是关于社群会不会得到金钱回馈。实际上,我们的项目是获得了“台北数位艺术中心(Taipei Digital Art Center)”的资金支持,对我们来说,去思考如何招募社群成员等问题是我们在来年的工作中需要面对的。就对大量的社群类项目来说,资金问题很重要一样,我们的出版项目也是真的极力将资金用于开源地出版,用于设计和发展着整个社群;但我也觉得一定在项目的某个角落,还存在着一些隐形的金钱问题,虽然资金问题对我和 Linda 这样的人群来说可能还相对简单,因为我们的背后有机构的支持,我们还可以向它们申请经费来运营我们的项目。
目前,我和我的同事们联合在 MIT Press 准备出版一套软件学习系列丛书。相比于着重在计算机科学视角看待软件,我们更倾向于将软件看作文化人工制品,是艺术、科学、人文和批判理论的混合。举个例子,我们中有人对批判理论中的种族议题也别感兴趣,我个人则是对酷儿和女性主义视角尤其感兴趣。像这样,我们希望打开软件学习在更多领域的交叉点。所以,在做的各位观众中如果有人也正在进行出版项目,如果你们感兴趣,可以将自己的 proposal 寄给我们。
张子木:谢谢 Winnie 的回应,现在我们也收集到两则对展销场工作的提问。
Slido提问 1:请问非展销场的出版物可以加入后勤慢递的网络吗?
Slido提问 2:慢递服务在最开始是怎么样成型的?购买的用户大概是什么样的人群?过海关的时候会有困难吗,怎么处理这些困难?
展销场:让我试着快速回应一下。关于第一个问题,那些想要被运送但不是我们发行范围内的书籍,取决于慢递员是否有能力运送。如果可能的话,我很乐意帮助人们。我们过去曾经做过,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缓慢而且要看是否有机会,所以不一定都能成功。但是如果有人有兴趣可以随时联系我。我是说,这个项目中我们还会携带其他比较敏感的物品,并不仅是书籍,所以这是要找到合适的匹配的问题。那些想要被运送但不是我们发行范围内的书籍,取决于慢递员是否有能力运送。如果可能的话,我很乐意帮助人们。我们过去曾经做过,但是这个过程非常缓慢而且要看是否有机会,所以不一定都能成功。
说到项目如何成型,还有购买用户大概是什么人群的问题,其实,这个项目其实是受到另一个艺术家的启发而诞生的。这个项目叫做“野生贸易”(Feral Trade)(参见:https://feraltrade.org/statement/ )是由一位名叫 Kate Rich 的商业艺术家在英国布里斯托尔开展的。她多年来一直在运营一种类似于配销服务的事业,为咖啡和其他食品产品提供相同的配销方式。我们非常感谢她对我们项目的启发。我们的兴趣点是出版,所以出版物成为我们运输的主要内容。对我来说,展销场最初创立并展开观察记录活动的兴趣主要来自于深圳和香港之间的跨境运输。因此,这些小规模的基础物品销售与资本全球化问题一直是我们开始做所有这些事情的核心原因。至于购买我们产品的人群,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项目只是关于友谊或只是通过朋友完成的,但是当然,因为这是以人际网络为基础的,很多项目始于我们认识的人和我们的朋友,因为ta们是我们知道的正在旅行的人。例如,如果我在艺术界工作,我发现帮助项目的人很多也会来自于艺术界。在某种程度上,这有点讽刺。我们基本上是利用了艺术界的特权,因为这些人是如今仍能进行旅行的人。但也不仅仅是这些人。有时,一些随机的、我们并不认识的人也会购买我们的产品。有些出版物我们在亚洲发行了,还有一些出版物没有,所以人们通过 Google 找到我们,因为 ta 们正在寻找特定的书籍。有些人是学者,有些人只是普通的年轻人。我们没有进行营销统计来确定每个人的身份。
张子木:还有关于海关的问题,你们是怎么和海关打交道的?
展销场:大多数情况下货物数量都很少,所以我们很幸运没有遇到这方面的麻烦。我想起有一次慢递员自愿加入我们的项目,但是 ta 们后来考虑到跨越边界时的敏感问题,所以最终不再与我们合作。但就目前为止,我们还是相当幸运的。
张子木:还有一个问题是:
“如何注册成为以为后勤慢递的慢递员?”
展销场:你可以通过网站注册(参见:https://displaydistribute.com/haukun/) 网站上有一个小的填空区域,你可以填写信息,也可以给我们发电子邮件,或通过 Instagram 等其他渠道联系我们,告诉我们你的旅行日期和目的地。我们会尽力为需要转运的书籍找到匹配。
张子木:谢谢展销场,我已经将相关连接发在了聊天框里,这样大家就可以去访问查看。接下来这个问题是问 Queenie 的。这位观众觉得 Queenie 的项目令人想到“微信阅读”:
“在微信阅读上,点击一本书中的某一个句子都显示出 ta 人的评论,也很有趣!请问您的这个读书会相对于这种已经商业化了的形式有什么更大的优势呢?毕竟微信阅读拥有巨大的用户群体。”
Kwan Q Li :感谢提问,我想我对何谓”优势”感到很好奇。我并不认为可以用用户的多寡和商业价值来衡量我们这个读书会的成功与否。我们更感兴趣的是如何创造一种与众不同的阅读体验。根据参与者的反馈,ta 们中的很多人就是享受很多人聚在一起做事情的想法。在世界的某个地方,有五六个不知名的人和你一起进行充满惊喜的阅读并交流感想,还有机会相遇并回顾整段经历,这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这也给了大家每周读书的动力。更重要的是,每位参与者首先需要先贡献出自己的阅读材料,分享给其他人,所以最后每位参与者都会收到包含了其他所有参与者的问题和思考的阅读反馈,我认为这种给予-接受的过程也可以与微信读书等商业性质的平台区别开来。
张子木:谢谢,目前为止没有其他问题了。或许各位讲者,你们对彼此的分享有什么问题或评论吗?
孙咏怡:我想就 Queenie 的分享说一说。我觉得刚刚听众针对 Queenie 的提问也显示出 Queenie 她们是如何在组织一场读书会的同时也创造出了一个另类的社群。我相信,每种工具都有它不同的影响面向,而不是单纯地符合它们“ABCD”般程式化的功能设定——例如你们设计的交流方式、或是如何把过程人性化、或是你们组织的方法。如果用 Linda 的话来说,就像是依靠规则的系统(rule based system),规则如何被设定?事情如何陆续发生?或许这一切也给你们的阅读创造了一个特殊的环境。
黎肖娴:Queenie, 现在有人想加入你们的读书小组了。
张子木:是展销场吧?
好的,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讨论还能拓展到更多的面向,所以它们不必被假设成特殊事件。我们的行动对应着我们所面对的境况,我们面对境况的解决方式也不一定就是完全理性可计算的,其中也有可能包含了大量诗意的的部分,大量挑衅、游戏的部分。
感谢今天到场的所有人,谢谢大家,Slido 上的问题会保存几天,欢迎各位在论坛结束后给我们留言评论,也欢迎各位嘉宾随时上 Slido 查看。如果黄孙权老师没有更多要说的,那么我想说,我非常荣幸组织了这场跨地域、跨语言文化,跨越各种边界的合作。感谢今天与会的每位嘉宾,在各自的时区里陪伴我们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也谢谢杭州的小伙伴们,还有今天的同声传译老师。大家晚安!